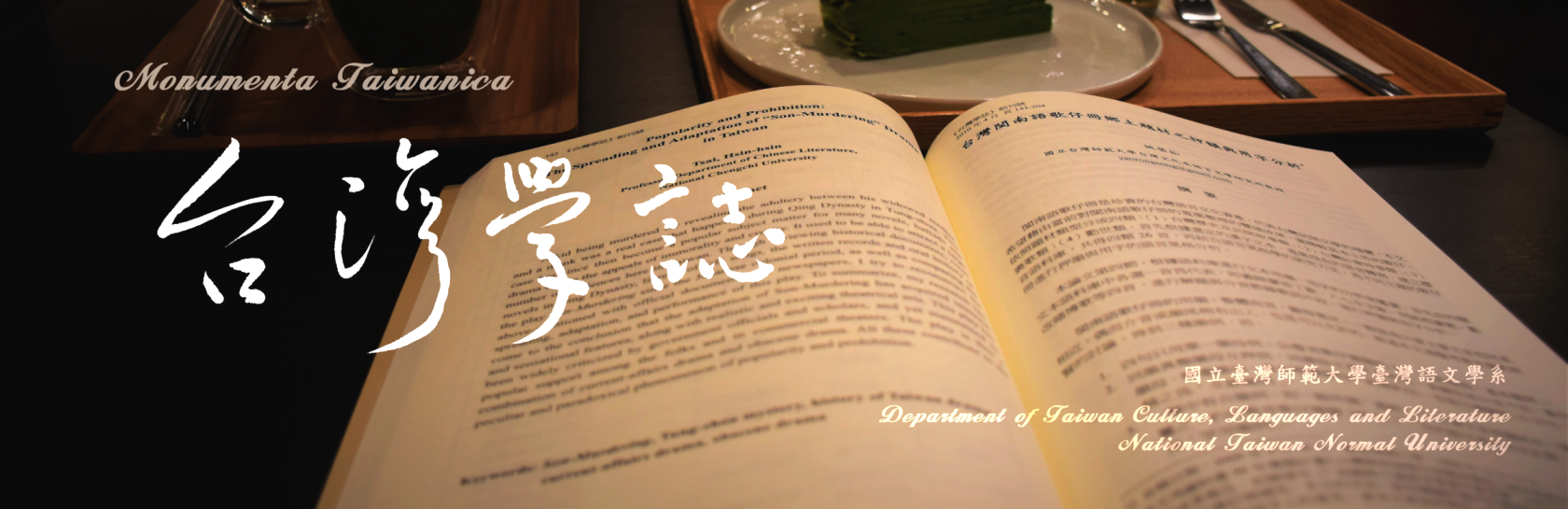| 摘要 |
1895 年(明治28 年)4 月清國依照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。當時,登陸澎湖群島及台灣島的日本軍翻譯官無法以官話(Mandarin)溝通,因此即時製作日語和台灣福佬話的對譯教材。為了與當地人溝通,當年6月至12月之間陸續出版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、《臺灣日用土語集(臺灣語集)》、《臺灣言語集》、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、《臺灣會話編》、《臺灣土語》、《臺灣語》等簡便的教材。本論文旨欲探討日人第一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,如何習得對方語言並且進行溝通,這個問題至目前為止仍尚待釐清。雖然幾項先行研究中,已對此議題提出初步的答案,包括筆談或使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及短句,且編纂對譯教材。然而,在筆者調查的教材中,仍然存在不符前述假設的情形。例如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、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裡,都發現有不使用媒介語言記錄台灣福佬話的案例。由此,本論文欲以維高斯基(Vygotsky)的語言習得、發展理論做為對照,探討人類在社會中獲得語言的方式,再者,如何從「外言」獲得「內言」,「內言」再連結到思考。這個觀點儘管是講述習得第一語言時的過程,卻暗示社會、語言的差異,如何影響到思考的過程。因此在分析最初期教材中的誤用時,甚有裨益。本文透過分析當初日人蒐集辭彙的方式、對譯、假名表記的方式,對照教材製作者的背景加以探討,並討論先行研究之成果,以期能逐步釐清日人首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的相關認知。 |